
海涅
2019-01-09
作为入行不算太久的编辑,我的好友栏暂时还没有被友站同行和甲方媒介占满,也没有自己的读者群。我的朋友圈大体上是由一些中轻度玩家、小部分的核玩家、完全不玩游戏的大学女孩、和一些自认为是女孩的男青年组成,零星还有几个江湖骗子。
这样一帮人,读书那会也算不上关系密切,平时最多聊聊D.va和天使的新皮肤,发几张黑色玫瑰的战绩图,到此就算是极限,却在某天一改往常的讨论起了独立游戏。
说来神奇,她们的话题最早从虚构的故事衍生至了现实中的事例,从游戏题材的伦理讨论上升到了危及社会的人类难题,起初我以为是一个像《The Red Strings Club》这样美术风格独特的赛博朋克游戏吸引了这些怪咖,缓过神才发现,话题的起因不过是一个橙光游戏,这也太荒唐了。

作为从业者,我似乎是最后一个知道这游戏的人
去年9月,这款游戏发布于橙光游戏平台,当时游戏圈讨论热度较高的话题是房地产公司跨界制作的国产武侠游戏《天命奇御》。这事动静挺大,我曾试着向她们阐述过这个还算可以的游戏是怎样在国产游戏圈里泛起了涟漪,却不怎么能提起这些人的兴致,和游戏行业的话题相比,她们更关心黄高乐是不是同性恋,混不混圈子。
在她们口中,这款游戏是一个现象级别的社会人文作品,在没有任何官方推荐的前提下,长期盘踞于橙光平台人气榜前列,微博大V对其赞不绝口,众多从来未曾涉足于游戏行业的自媒体纷纷为其自发撰文写稿,豆瓣用户评分9.2,社会反响之强烈就差用新XX运动来定义,对于我这个从业人员的无动于衷她们表示强烈的不解,笃定我是一个后知后觉,假的新闻工作者。
实际上从知道这个游戏,到玩这个游戏之间,我酝酿了足足两个半月,比暑假还长,一直没尝试这个游戏的原因很简单,我认为这种“制造处境让不同立场的人产生共情,再相互理解”的做法是矫情的,没有人能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即使感动一时,几天后也就忘了。如果一个“网页游戏”能让这个沉积已久的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哪怕是得到舒缓,那也太小看社会矛盾了吧。
在这两个半月里,从10月份开始,无数的公众号开始推送这款游戏的相关内容。如何与同性恋相处成了媒体们的新热点,但迫于kpi的压力,大多都是新媒体小编不曾核实随手捏造的五六七八手故事相互复制粘贴。在网络大数据的支持下,我平时浏览的视频网站也开始频繁推送LGBT内容,这大大加深了我的抵触情绪。打开网络,似乎同性恋已经脱离弱势群体,或者说整个世界呈现一片安宁,仿佛21个世纪的人类文明历史上从来不曾存在过同性恋歧视,一种由舆论环境造成的过分融洽且和睦的关系让我难以心安。
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或者说我是一个反同性恋者,与此相反我是个对同性交往毫无抵触的普通人,我只是反感这种由游戏题材引发的网络现象,强迫他人选立场站队。在这个游戏出现的短时间内,似乎任何一个再微小不过的异样声音,都活该被千刀万剐,强迫其戴上不懂何为爱,何为尊重的大高帽,周围的看客们还瞠着眼睛一阵阵的叫好,他们昨天还在为喜欢的角色变成了gay而对此深恶痛绝来着,一时间全天下只允许有一种声音,我差点就以为,国内大环境下的同性恋们已经过上了幸福且自由的生活。
想也知道这不可能,越激烈的言辞越容易引起反抗情绪,现实中的矛盾并不会像打台球一样“大力出奇迹”,刻意的潮流让当事人们无所适从,被旖旎的表象所桎梏住的少数群体,正被社会余响压得踹不过气,有口难辩。
放在游戏中,“她”就是几乎符合一切需求的“女主角”
Emran的汉语名是伊木兰,将维语译作这三个汉字写在身份证上的是她小学的语文老师。89年带着“把儿”出生在伊宁县的一个小镇上,水泥堆砌的楼房旁是一座清真寺,童年时期的每个周末她都在这里度过。
维吾尔族,性别认知障碍,同性恋,穆斯林,宗教人士,准确的说是前宗教人士,这些都是属于她的标签,我和她认识时就已经是这样了。和一般人念想里的“女装大佬”不同,兰从来不穿裙子,着装方面和普通男生无异,只在特别的地方花费心思,看起来就是一个慵懒的当代标准腊肉,80年代出生的愤青最后都是这样。她的眼距很窄,琥珀色的瞳孔,发量刚好及肩,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她爽朗的笑容和眉宇间的一丝阴柔,偶尔歇斯底里,却坚强的像个男生,这是她与我所有认识的跨性别者最大的不同。
兰女士喜欢修身的水洗牛仔裤,穿鞋1米82,有一个高挺的鼻子,面容的辨识度极高,学了几句法语后更是以假乱真,我们在霍尔果斯的酒吧喝酒时,靠这招骗过不少老外。念书那会她还组过乐队,不管是冬不拉还是电贝斯都手到擒来,但不爱跳舞,因为没人教她民族舞中的女性步伐。
私下里,兰喜欢打电动,酷爱《血缘》和魔兽RPG,偶尔补补老番,热衷于一切看起来很朋克的玩意,比如稀奇古怪的Chocker,我爸管这个叫狗链子。
独处时会消耗北京卷烟厂制造的中南海牌香烟,但从不喝酒,没有摄入酒精的需求,用她的话说,酒吧里的一切行为不过是配合气氛而已,这也是她最擅长的。

NANA是兰最喜欢的女性形象,但她认为大崎娜娜偏爱的七星太呛了
她记不清自己是在何时显得与其他男孩不太一样了,好像懂事起就已经如此。我试着拼凑了一些她酒后的故事,深夜的聊天记录,梦里的喃喃自语,期望找到她的心结,但不能保证其中的真实性。

1999年,北京的新蜂音乐为大张伟发行了早期中国最朋克的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I》,那时她10岁,镇上的磁带店里偶然听过《静止》。这一年,兰出生以来第一次因为生病以外的理由住院了,因为药物食用过量,同行的还有她的母亲,送她们母子到医院的是兰的叔叔。将这件事简单概括就是,一位30岁的母亲无法忍受来自丈夫的暴力,最终选择和自己的孩子离开世界,未遂。
每当聊起这件事时,兰总是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的父亲,将这个男人形容成狡猾且恶毒的野兽,表面上他是个虔诚的信徒,乐善好施,平易近人,暗地里却是她们母子的梦魇,以折磨亲人为乐,说这话时她的神态看起来镇定无比,似是未曾惧怕过,话里尽是旁人难以理解的厌恶。
当说到她的母亲时,这个差点夺去她性命的人则被形容成一位伟大的女性,生活中对她关怀备至,是唯一能让她感受到温暖的人,她将母爱歌颂为最伟大的人类羁绊,称其为独属于女性的情愫,只是有些时候母爱的体现方式不太妥当罢了,而这些不太妥当的做法又因为她父亲的存在,演变的合情合理。
兰对女性身份有着超乎寻常的固执,热爱游戏的她并不在意人们用欧美文化中的那套“政治倾向正确的主角命”来调侃她,只要保证是女主角即可。但小时候的她并不像现在这样跋扈,而是压抑自己,扮演一个出色的男性形象。
18岁那年的成人礼,兰遇见了一个能让自己敞开心扉的KZ女孩,关于女孩的事她总是闭口不谈,仿佛要把所有的美好只留给自己,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兰的追求失败了,作为男性的立场。至于她的第二次追求,还没来得及展开,女孩就去北京读预科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人生路上、心理旅程的分岔路,但她在19岁时选择了像母亲摊牌,用最炙热的词汇描述了自己对于女性的喜爱,我想这时候她母亲的大脑应该是放空的,换位思考一下,当你听到一个身份证上写着性别男的帅小伙对你说他喜欢女人时,能有什么想法?
为此,她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向母亲解释其中的复杂关系,兰曾以此问过我“你觉得我妈会怎么说?”
当初我认为,兰的状况应该是所有同性恋都羡慕乃至嫉妒的境遇,生理性别男,性取向女,从表面上看,似乎她可以顺理成章且合法的在我国境内恋爱,甚至结婚,那么她的母亲即使万般不能理解,也不会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事,毕竟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看出来这对郎才女貌的“正常人”是同性恋呢?
但我忘了的是,她的母亲是可以带着10岁的孩子往地狱里跳的人,不管表面上兰的行为多么正常,她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宗教信徒对于精神世界的戒律有着更加纯粹的偏执。理所当然的,兰被赶出了家庭,离异后兰的母亲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并将她的“女儿”从伊斯兰教里革了名,因为《古兰经》非常明确的谴责了同性恋行为。

《古兰经》中也明确禁止了信徒的自杀行为,这是故事中我最难理解的地方,兰用“这就是大人”回答了我
辍学后的兰开始了四处奔波的生活,她的性格也由此定性,我经常问她后悔吗,她总是能说出千百个理由堵住我。不用再去清真寺做礼拜是她挂在嘴边最常说的话,那里不仅否定了兰的一切,还要求兰跟着“奶妈子”念诵的经文一起痛斥有违天伦的同性恋行为,她需要尽可能的压抑一切关于自己的情感,才能保证双重否定不变成肯定,现在一身融入气氛的功夫,可能就是那时练成的。

清真寺内一般是不允许拍照的,所以我放一张伊宁“东正教”的仪式照片参考,他们属于基督派系,虽然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这些宗教活动并不是什么神秘邪乎的事物。来自Vice
在这段时间里,兰作为我朋友圈中对《A Gay's Life》这款游戏最有发言权的几人之一,却并不怎么热衷于讨论这个话题。我知道她肯定不是没有想法,选择不说也一定是有意为之的配合气氛,所以我在11月的一个周末里单独约见了她,在上海的一家小酒吧里,和环境不大匹配的是,店里循环播放着《Tea For Two》。
久违蒙面的她依然是一副爽朗的笑容,互相问好后我们照常坐在吧台最显眼的位置,这里很方便于我们扫视整个店里各式各样的人,通过他们的穿着、表情、酒种来对其为人瞎猜一通,不做证实,只当谈资,有时候酒保也会加入我们,让游戏变得没有乐趣。
兰落座后先礼貌的询问了酒保能否换一首音乐,被拒绝了,你爱听不听。我趁着空档,率先向兰发起了攻势:“如何评价《A Gay's Life》这款游戏?”标准的知乎体。
“能这么问,说明你还没有玩过,这游戏有段时间了,作为从业者却不曾玩过,说明你并没有重视它。”
兰并没有给我反驳的机会,她的想法像自言自语般娓娓道来:“《A Gay‘s Life》这个游戏算不上多么有份量,只是这些年随着同性恋去病化,性取向错误不再是精神疾病后的现在,LGBT才成为了被人们所重视的人权底线,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所以只要话题足够有争议,任何一个看上去是那么回事的东西都可以达到现在的效果,何况你们游戏行业的本家媒体都不怎么报道过这款「游戏」,可见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伟大。
说起来挺悲哀的,一款「游戏」没有在游戏圈里泛起波澜,却被对此熟透了的小群体奉若百科全书,需要了解的人不曾知道,一群没救了的人翻了又翻,你说讽刺不讽刺,你写了一首自认为牛X的堪比99年《稻草上的火鸡》的朋克摇滚,却只有你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表弟堂妹点赞,能高兴的起来吗,过几年都没人记得了。互联网让这些少数人群找到部落,网络让他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可实际上呢,互相理解的还是这群同性恋,你们异性恋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不仅如此,嘴巴上还总说着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真碰到了还不是敬而远之,因为同性恋,我在北京三个月被炒了四次,从三里屯的公寓搬到劳动街的青年旅馆,同性恋这标签比身份证上的新疆省还要刺眼,但我必须忍着。海涅,假若我在微博上提了这么一句,马上就要迎来连番的审问,他们甚至和我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际。「你们同性恋得到的宽容还不够多吗?」百口莫辩!
假若是10年前,我可能会因为这个游戏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我已经不算年轻了,却还流浪于城市间做着手艺活儿,无家可归,游戏里的结局我早就已经走过一遍,自己就是个Bad Ending,对所离甚远的成功也无法感同身受的高兴,我只能体会坏结局中的绝望,仅此而已。和那些正在路上行走的人不同,他们还能被鼓励,还有着可能性,但我已经不能继续骗自己了。10月份我试着玩了下《The Missing: J.J. Macfield and the Island of Memories》,它更适合当下的我。我需要的不再是一个由虚构情景促成的共情,由不确定的过程带来的结果并对其解读,这本应该是你们需要的。
海涅,我的兄弟,在中国,同性恋没有未来。”

失踪的J.J.讲述了一个关于跨性别、同性恋的故事,是一场找寻自我的旅程,但它仅仅描绘了过程
绝望的话语和一饮而尽的空酒杯,是她留给我最后的讯息。随着酒精的发酵,她的话语开始反复在我的脑内播放,押着爵士乐的节拍,一字一句。
我认为她太悲观了,被赶出家庭以后的她开始沉溺于自己的世界,一直配合气氛的她开始了晚年叛逆,吃不饱的人才显得朋克。我能理解她对于未来的放任,她已经不在乎以后了,她只想找回自己,弥补这么些年的空缺。
极端的故事让我难以将它当做一个完整的例子,我本来以为自己对于同性恋已经足够了解,兰的话语却让我对她们的认识越发模糊,我虽然不认为当代同性恋的处境是乐观的,也难以接受这样决绝的答复。为此我需要一些新鲜血液来把我说服,让那些还没有走过「结果」这一步的人阐述他们的想法。
年轻的Gay告诉我,承受压力是不可免的过程,至于结局,他还在路上呢
12月18日,触乐网的刘淳老师为《A Gay‘s Life》撰写了一篇文章,我惊讶的发现这个游戏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烂俗,共情不过是其中一个元素,严肃的互动科普才是它的本质。借由这个契机,我尝试着打开了这款游戏。
因为我身边圈子不乏比游戏描述更为触目惊心的故事,所以游戏中的剧情起伏并不会让我有太多预料外的触动,但游戏确实完整的还原了一部分同性恋的真实心理,甚至为那些踌躇犹豫的人们提前打好了预防针,对于兰来说这个游戏太小清新了,但对那些未经社会正彷徨着的人们来说,这个游戏充满了人情味。
我曾一度认为自己的朋友们被环境所同化,失去了个性,档次和格调都在以光速下降,没想到,是我没追上她们的境界,我为自己的眼高手低感到羞愧。游戏流程过后,我心中有了新的采访对象。
你们可以叫他叶先生,或者小Y。Dead Game最盛行时他随我一起入坑,最钟爱的英雄是暗影猎手,而暗影猎手的昵称小Y,亦是他姓氏的打头字母,我们便习惯性忽略他自傲的姓氏,直接叫他小Y。
小Y是个胖子,没什么特点,生的白白净净,刘海齐眉,低头看不见脚趾,伸手摸不到后背,标准的当代二次元宅男臆想形象,但他本人对于二次元甚少产生兴趣。1998年出生在四川,来新疆的原因很简单,高考分数线低。

去年12月末,我联系到了在上海念书的小Y,趁着元旦假期在酒吧里碰了头,上次来这里是和兰一起。
我们照常坐在散台的角落,靠近酒柜的位置,这里的视野很适合观察来这里的人们握酒的姿势,小Y喜欢看人的侧脸,将自己隐藏起来。店里放着Nujabes的《Aruarian Dance》,店家似乎听取了一些我的意见。

瀬葉淳是Jazz—Hiphop届的灵魂人物,2010年因车祸丧生
《混沌武士》是少数能让他提起兴致的Tv动画,我凝视着随节奏律动的小Y,发现他还是那样没什么特点,完全无法令人产生攀谈的欲望。借着酒精,我试着询问了他的近况和一些有的没的。
他语速极快,用着勉强算是工整的话语:“听说你玩过了《A Gay’s Life》?那可真不错,你们需要试试这个,而不是我们。前段时间兰向我发了一通毫无道理的飙,我猜是因为你,具体原因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比如现在。
你想从我这了解些什么,渲染一番发到网上去引起共鸣,没问题,我帮你就是了。
最近几年过的还行,我害羞的人设已经深入人心,借着猎空这些话题形象也试着同身边关系好的人出柜了,也许是几年的相处让他们并不介意,至少现在和同学们表面的关系都还不错。9月份借着这个游戏,我在学校社区里认识了另一个Gay,我们虽然没什么发展,但成为了要好的朋友,身边的人总比网上的朋友、远在另一个城市的朋友靠谱一些。
《A Gay‘s Life》这个游戏虽不至于改变我的人生,倒也让生活多了几分坚定,有人能为你发声是件好事,可能短时间内会有一些过分极端的压力让你不知所措,但任何改变都伴随着这样的风险。我这人没什么内涵喜好跟风,你们吹《星际牛仔》我就关注渡边信一郎,你们听LoFi我也跟着听ROOK1E,我说不出太多意有所指的语言但你们说的我都能勉强明白,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毕业以后我就打算和父母正式出柜了,我觉得他们也应该猜出了一二,只是在等我点破罢了,没被赶出家门,说明事情还有的聊,希望一切顺利吧。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有好有坏,有反面的例子必然有正面的模范,你看我这路不还走在脚下吗。
海涅,你是游戏媒体人,应该将重心放在游戏传播上,而不是我们这些人,说到底,《A Gay‘s Life》是属于你们的游戏,让你们了解我们的游戏,自我抒导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些人基础中的基础,它对我们的意义比你想象中要小得多,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和你一样有几个同性恋朋友,更多的人在生活中接触不到这存在于社会夹角,蜷缩在缝隙里的人,他们无法直击这些隐藏在社会表层之下,扎根在人性里的扭曲,他们只能凭借脑海里的刻板印象去评判从未接触过的群体,这里面有太多别人不懂的情绪,你再神的键盘也敲不出贴切的文字「有效」传递出能产生共情的信息,远不及一个完整的系列故事,所以我才觉得这游戏有那么点意义,对你们来说。
前段时间我还买了《The Red Strings Club》,它是适合我们的游戏,当然你们也可以试试。游戏的结局会面临两个选项——在世界陷入黑暗,你人生的最后一秒里,是将事件的真相告诉他,还是告诉电话那一头的多诺万你的感情,我玩了10多遍,分支选项都不曾重合过,唯独故事的结尾我总会选择「多诺万,我他妈的爱死你了」。
如果你有兴趣且试过了,务必告诉我另一个选项的结局,你肯定不会和我选择一样的。”


《红弦俱乐部》,玩家在调查连环事件的过程里发现了世界的秘密,在既定的坠楼结局画面,有两个选项,它们都代表着真实。
每次和小Y的聊天,都让我意识到同性恋不过是一群内心敏感的孩子,和我们的经历,对事物的解读没什么区别,只有立场上的不同,曲折的故事属于少数中的少数人,并不需要刻意修饰这些人的生活。上海念书的日子里,小Y会参加一些本地的同性恋公益活动,大家的处境都算不上乐观,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羸弱,现实里有太多迫切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睡在三和的网咖里,甚至丢失了身份证也毫不在意,与这些已经放弃了生活的人相比,同性恋远远还没有达到需要媒体高度曝光全民拯救的程度,对于好心人的援手,他们表示谢意,对于玩笑性的调侃,他们表示理解,千万不要刻意掩饰某些行为,或是假装不知道,刻意回避些莫须有的东西,太疏远了。
我希望小Y在和父母出柜以后也能如此积极,打从心里,我不希望他成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谁。
虽然九几年那会,美国有个摇滚哥们对着摄像机嘶吼着“在这里,没有未来。”但你看看现在,《All Out Life》这张专辑你听了吗?
——Old does not mean dead, new does not mean best
No hard feelings, I'm tired of being right about everything I've said
Yours does not mean mine, kill does not mean die
We are not your kind。
明天的事,后天就知道了,现在胡扯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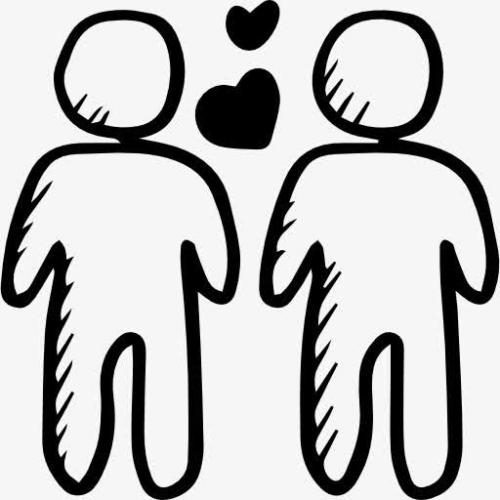
编者按:明天的事,后天就知道了来源于我儿时的一句玩笑话,长大后我常在思考明天的事难道不是明天就知道了吗,那么它意义在哪,我想这大概就是对于事物结局的非理性阐述,结局也并非一成不变,明天的Bad Ending也可能在后天反转,当下没有希望,不代表明天没有未来。












玩家点评 (0人参与,0条评论)
热门评论
全部评论